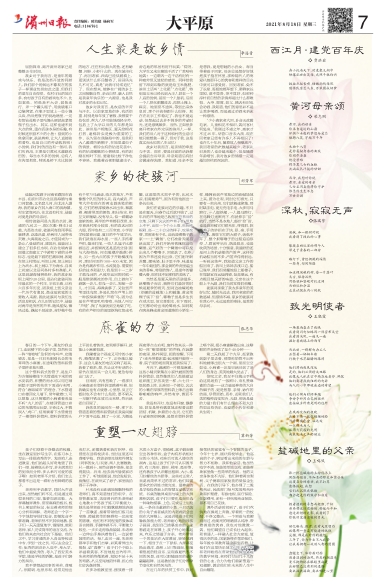发布日期:
人生最是故乡情
屈指算来,离开滨州老家已经整整25年时间。
故乡对于我而言,是童年的嬉戏与快乐。我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,我们那个时候远不像现在的孩子一样课业负担如此之重,但我们的童年自由得很。农村可玩的地方多,农村孩子自有的游戏也不少,比如套鱼。钓鱼我不大会,套鱼还行。弄一个罐头瓶子,用线绕瓶口边缘绑紧,在瓶子里放上一些小馒头块,然后把瓶子扔到池塘里,一见有鱼钻进瓶子里吃馒头屑就赶紧把瓶子拉出水。其实,这样也逮不到大点的鱼,重在活动本身的乐趣,有时候还很套不少的小鱼!套到的小鱼拿回家,洗洗剪剪,让大人直接油煎着吃,也是自己的劳动收获呢!小时候,我们村的西边有一条河,我们叫西沟,主要是引黄河水灌溉农田的。每当水不多的时候,总有人在沟里抓鱼,特别是桥下水比较深的地方,往往有比较大的鱼,还有螃蟹、河蚌、小虾什么的。现在城市化了,再回老家,西沟已经快被填上,更别谈什么虾兵蟹将了,田园风光几不可见,真是“此情可待成追忆”了。现在想来,能够在广阔的乡土之间接触自然、亲近自然、融入自然是我童年快乐的一大源泉,也是我对故乡的永恒记忆。
故乡对我而言,是农活的辛劳与汗水。以前家里地很多,农活很重,特别是每年放了暑假,我都要干些农活,帮大人尽可能地减轻辛劳,包括上了大学以后的几年都是如此。滨州是产棉地区,夏天给棉花打药、逮棉铃虫是极为重要的工作。长久留在我脑海中的,是我和大人戴着防晒帽子,在地里逮虫子的情景。棉铃虫有的钻进花蕊中,有的钻进嫩嫩的小棉桃里,有的则藏在棉叶下面,要逮得比较干净也不容易。我戴着近视眼镜逮虫子,旁边地的邻居有时开玩笑:“哎呀,大学生又来庄稼地干活了!”我哈哈地笑!一边聊天一边干活有时有一种疲劳但又放松的感觉。同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给玉米施肥,滨州土话叫“上化肥”“点化肥”,特别是玉米已经长到大半人甚至一个人高的时候,前面一个人刨坑,后面一个人把化肥撒进去,再把土掩上、踩实。地里密不透风,等到出来休息时,那个汗流得跟什么似得。现在在北京工作稳定了,我也不爱运动,但想起过去并不算多的劳动时光,还是感慨颇多。当然,正如很多离开老家在外定居的滨州人一样,我们的后人对于这种农村的生活可能只能想象一番了,但对于我,这是真实而永恒的人生记忆!
故乡对我而言,是亲情的牵挂与不舍。现在,要是回家的话我都会提前告诉母亲,母亲知道后有时会激动得失眠。我知道,母亲不仅是想我,更是想她的小孙女。每当带着孩子回家,母亲总是想好好地把孩子抱在怀里,那种隔代人的疼爱从她那开心的笑容和慈祥的目光中就可以感受到。回到老家,免不了长辈、哥姐地都拜望下,聊聊家长里短,酒不算贵,茶不算好,但那种淳朴而自然的亲情却是比什么都难得。大爷、舅舅、姑父、姨夫有时也会劝酒,我知道,他们的意思并不是让我多喝酒,而是通过劝酒来表达一种感情。
“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,笑问客从何处来。”我刚过不惑之年,离家才不过25年,尽管口音未大改,现在回老家已经有许多人不再相识了!也许几十年后,随着故人相继离开,我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,老家认识我的人也会越来越少,但是随着年龄增长,我对故乡的情感一定是越加炽热而深沉的。
故乡对于我而言,是童年的嬉戏与快乐。我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,我们那个时候远不像现在的孩子一样课业负担如此之重,但我们的童年自由得很。农村可玩的地方多,农村孩子自有的游戏也不少,比如套鱼。钓鱼我不大会,套鱼还行。弄一个罐头瓶子,用线绕瓶口边缘绑紧,在瓶子里放上一些小馒头块,然后把瓶子扔到池塘里,一见有鱼钻进瓶子里吃馒头屑就赶紧把瓶子拉出水。其实,这样也逮不到大点的鱼,重在活动本身的乐趣,有时候还很套不少的小鱼!套到的小鱼拿回家,洗洗剪剪,让大人直接油煎着吃,也是自己的劳动收获呢!小时候,我们村的西边有一条河,我们叫西沟,主要是引黄河水灌溉农田的。每当水不多的时候,总有人在沟里抓鱼,特别是桥下水比较深的地方,往往有比较大的鱼,还有螃蟹、河蚌、小虾什么的。现在城市化了,再回老家,西沟已经快被填上,更别谈什么虾兵蟹将了,田园风光几不可见,真是“此情可待成追忆”了。现在想来,能够在广阔的乡土之间接触自然、亲近自然、融入自然是我童年快乐的一大源泉,也是我对故乡的永恒记忆。
故乡对我而言,是农活的辛劳与汗水。以前家里地很多,农活很重,特别是每年放了暑假,我都要干些农活,帮大人尽可能地减轻辛劳,包括上了大学以后的几年都是如此。滨州是产棉地区,夏天给棉花打药、逮棉铃虫是极为重要的工作。长久留在我脑海中的,是我和大人戴着防晒帽子,在地里逮虫子的情景。棉铃虫有的钻进花蕊中,有的钻进嫩嫩的小棉桃里,有的则藏在棉叶下面,要逮得比较干净也不容易。我戴着近视眼镜逮虫子,旁边地的邻居有时开玩笑:“哎呀,大学生又来庄稼地干活了!”我哈哈地笑!一边聊天一边干活有时有一种疲劳但又放松的感觉。同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给玉米施肥,滨州土话叫“上化肥”“点化肥”,特别是玉米已经长到大半人甚至一个人高的时候,前面一个人刨坑,后面一个人把化肥撒进去,再把土掩上、踩实。地里密不透风,等到出来休息时,那个汗流得跟什么似得。现在在北京工作稳定了,我也不爱运动,但想起过去并不算多的劳动时光,还是感慨颇多。当然,正如很多离开老家在外定居的滨州人一样,我们的后人对于这种农村的生活可能只能想象一番了,但对于我,这是真实而永恒的人生记忆!
故乡对我而言,是亲情的牵挂与不舍。现在,要是回家的话我都会提前告诉母亲,母亲知道后有时会激动得失眠。我知道,母亲不仅是想我,更是想她的小孙女。每当带着孩子回家,母亲总是想好好地把孩子抱在怀里,那种隔代人的疼爱从她那开心的笑容和慈祥的目光中就可以感受到。回到老家,免不了长辈、哥姐地都拜望下,聊聊家长里短,酒不算贵,茶不算好,但那种淳朴而自然的亲情却是比什么都难得。大爷、舅舅、姑父、姨夫有时也会劝酒,我知道,他们的意思并不是让我多喝酒,而是通过劝酒来表达一种感情。
“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,笑问客从何处来。”我刚过不惑之年,离家才不过25年,尽管口音未大改,现在回老家已经有许多人不再相识了!也许几十年后,随着故人相继离开,我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,老家认识我的人也会越来越少,但是随着年龄增长,我对故乡的情感一定是越加炽热而深沉的。